徵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是台中豐原稅務功能運作最佳稅務後盾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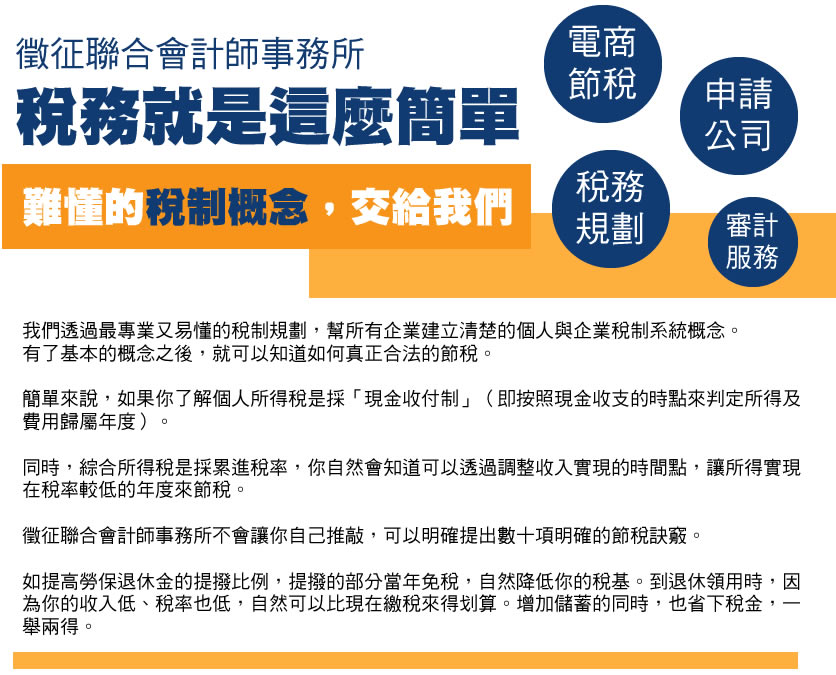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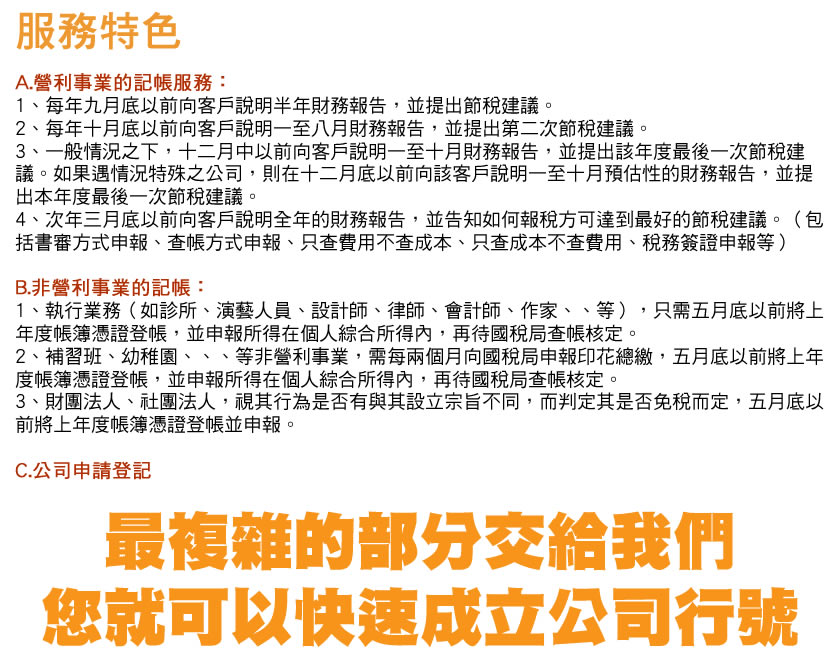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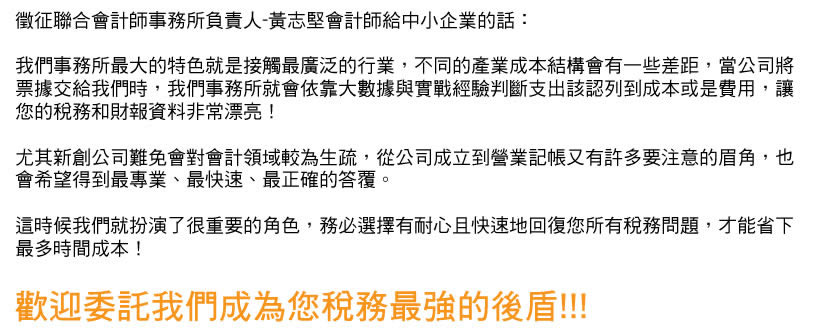
台中西屯國稅局查核案例分享, 台中北區家族稅務及傳承規劃, 台中大里創業家移民會計服務推薦
巴金:馬賽的夜 馬賽的夜。 我到馬賽這是第二次,三年以前我曾到過這里。 三年自然是很短的時間,可是在這很短的時間里我卻看見了兩個馬賽。 寬廣的馬路,大的商店,穿著漂亮衣服的紳士和夫人,大的咖啡店,堂皇的大旅館,美麗的公園,莊嚴的銅像。我到了一個近代化的大都市。 我在一個大旅館吃晚飯。我和兩個朋友占據了一張大桌子,有兩個穿禮服的漂亮茶房伺候我們。我們問一句話,他們鞠躬一次。飯廳里有樂隊奏樂。我們每個人點了七八十個法郎的菜,每個人給了十個法郎的小賬。我們從容地走出來,穿禮服的茶房在后面鞠躬送客。 我們又到一家大咖啡店去,同樣地花了一些時間和一些錢。我們在“多謝”聲中走了出來。我們相顧談笑說:“我們游了馬賽了。”心里想,這畢竟是一個大都市。 于是我們離開了馬賽。三年以后我一個人回到這里來。我想馬賽一定不會有什么變化。而且我把時間算得很好,我不必在馬賽住一夜。我對自己說:“我第一晚在火車上打盹,第二晚就會在海行中的輪船上睡覺。” 然而我一到馬賽,就知道我的打算是怎樣地錯誤了。第一,我一下火車就被一個新認識的朋友引到了一個奇怪的地方,這個地方使我覺得我不是在馬賽,或者是在另一個馬賽;第二,同那個新朋友到輪船公司去買票,才知道今天水手罷工,往東方去的船都不開了。至于罷工潮什么時候會解決,辦事人回答說不知道。 這樣我就不得不住下了,而且是住在另一個馬賽。至于在海行中的輪船上睡覺,那倒成了夢想。 于是我又看見了馬賽的夜。 我住的地方是小旅館內五層樓上一個小房間。 我吃飯的地方也不再是那堂皇的大旅館,卻是一家新近關了門的中國飯店。吃飯的時候沒有穿禮服的茶房在旁邊伺候,也沒有樂隊奏樂。我們自己伺候自己。 這并不是像紐約唐人街一類的地方,這的確是法國的街道。中國人在這里經營的商店,除我所說的這個飯店外,還有一家飯店,要那一家才算是真正的飯店。至于我在那里吃飯的一家,已經關了門不做生意,我靠了那個新朋友的介紹,才可以在那里搭一份伙食。而且起先老板還不肯收我的飯錢。 我每天的時間是這樣地分配的:從旅館到飯店,從飯店到旅館——從旅館到飯店,從飯店到旅館。在旅館里,我做兩件事:不是讀一本左拉的小說,就是睡覺,不論在白天、晚上都是一樣。在飯店里我也做兩件事:不是吃飯,就是聽別人說笑話。吃飯的時間很短,聽說笑話的時間很長。 從旅館到飯店雖然沒有多少路,可是必須經過幾條街。我很怕走這幾條街,但我又不得不走。路滑是一個原因:不論天晴或者下雨,路總是滑的;地上還凌亂地堆了些果皮和拋棄的蔬菜。街道窄又是一個原因:有的街道大概可以容三四個人并排著走;有的卻是兩個人對面就容易碰頭的巷子;也有的較寬些,但是常常有些小販的貨車阻塞了路。我常常看見胖大的婦人或者瘦弱的姑娘推著貨車在那里高聲叫賣,也有人提了籃子。她們賣的大半是蔬菜、水果和襪子一類的用品。有一兩次,賣水果的肥婦向我兜生意,可是我跟她剛把價錢講好,她忽然帶笑帶叫地跑開了。跑的不止她一個人,她們全跑開了。街道上起了一陣騷動,但是很快地就變得較為寬敞、較為清靜了。我很奇怪,不知道這個變化的由來。但是不久我就明白了。迎面一個警察帶著笑容慢慢地走過來。他的背影消失以后,那些女人和貨車又開始聚攏來。有時候抬起頭,我還會看見上面曬著的紅綠顏色的衣服。 還有一個原因我也應該提一下,就是臭。這幾條街的臭我找不到適當的話來形容。有些地方在店鋪門口擺著發臭的死魚,有些地方在角落里堆著發酵的垃圾,似乎從來就沒有打掃干凈。我每次走過,不是捏著鼻子,就是用手帕掩鼻,我害怕會把剛吃進肚里的飯吐出來。 晚上我常常同那個新朋友在這些街道上散步,他帶笑地警告我:“當心!看別人把你的帽子搶了去!”我知道他的意思。我笑著回答:“不怕。”不過心里總有點膽怯,雖然我很想看看帽子怎樣會被人搶走。 我們走過一條使我最擔心的街道。我看見一些有玻璃窗門的房子和一些掛著珠串門簾的房子。門口至少有一個婦人,大半很肥胖,自然也有瘦的,年紀都在三十以外;她們同樣地把臉涂得又紅又白,嘴唇染著鮮血一樣地紅;她們同樣地有著高高地凸起的胸部和媚人的眼睛。 “先生,來罷。”尖銳的、引誘的、帶笑的聲音從肥婦的口里向我臉上飛來。同時我看見她們在向我招手。 “怎么樣?去嗎?”那個朋友嘲弄地低聲問我。 我看了那些肥婦一眼,不覺打了一個冷噤,害怕起來,便拉著朋友的膀子急急地往前面走了,好像害怕她們從后面追上來搶走我的帽子一樣。我走過那些掛著珠串門簾的房子,里面奏著奇怪的音樂,我仿佛看見三四個水手抱著肥婦在那里喝酒。但是我也無心去細看了。 “你方才說過不怕,現在怎樣了?”我們走出這條街以后,那個朋友嘲笑地說。 我這個時候才放心了。 “看你這個樣子,我不禁想起我一個姓王的朋友的故事。”他說著就出聲大笑。 “什么故事?”我略帶窘相地問他。 “王,你也許認識他。他的年紀比你大,可是身材比你還小,”朋友開始敘述故事,他一面說,一面在笑。但是我并沒有笑的心思。“他是研究文學的。他常常說歌德有過二十幾個愛人,他卻只有五個,未免太少了。其實他所說的五個,是把給他打掃房間的下女,面包店里的姑娘,肉店里的女店員都算在里面,這些女人跟他除了見面時說一聲‘日安’外就不曾說過什么話。他說他應該找到更多的愛人,他說應該到妓院里去找。我們每次見面,他總要對我宣傳他到妓院去談戀愛的主張,他甚至贊美賣淫制度。然而他也只是說空話。我常常嘲笑他。有一天他得意地對我說,他要到妓院去了,我倒有點不相信,你猜他究竟去了沒有?”朋友說到這里突然發出這句問話來。 “他當然沒有去。”我不假思索地回答。 “他如果沒有去,那倒不奇怪了。他的確去了,而且是我陪他去的。”朋友得意地說。“他沒有進過法國妓院,他不知道那里面的情形。我們到了那里。我聲明我只是陪伴他來的,我就坐在下面等他。于是六七個肥胖的裸體女人排成一行,站在我們面前,讓王選擇。王勉強選了一個,在下面付了錢,跟著她上樓。……不到十分鐘,王下樓來了,臉色很不好看。他拉著我急急地走了出去。我驚奇地笑問他:‘怎么這樣快就走了?’他煩惱地答道:‘不要提了,我回去慢慢對你說。’他垂著頭,不再說一句話。”朋友說到這里,便住了口。 “你看這個。”他從衣袋里摸出一封信遞給我說。“這是王今天寄來的,他還提到那件事情。” 這時我們走入大街,進了一個咖啡店。我在那里讀了王的信。 信里有這樣的一段話: ……近來常常感到苦悶,覺得寂寞,精神仍然無處寄托,所以和幾個朋友在一起談話時總愛談到女人。大家都覺得缺少什么東西。可是缺少的東西,卻也沒法填補。我們也只得耐心忍受苦悶。壯志已經消磨盡了。我也曾想把精神寄托在愛情上,但是又找不到一個愛我的女人。……我也不再有到妓院去的思想了。用金錢買愛,那是多么可笑,多么渺茫啊!你不記得兩年前我在馬賽干的那件事嗎?我當時還有一種幻想。誰知看見了那里的種種丑惡情形,我的幻想就馬上破滅了。我和那個肥婦上了樓,進了她的房間,看見她洗凈了身子。我沒有一點熱情,我只覺得冷。她走到我的身邊。我開始厭惡她,或者還害怕她。她看見我這種笨拙的樣子,便做出虛偽的媚笑引動我,但是并沒有用。我的激情已經死了。結果她嘲笑地罵了我兩句,讓我走了。從那里出來,心上帶走了無名的悲哀,我整整過了一個月的不快活的日子。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緣故。我在那里不但不曾得著預期的滿足,反而得到了更大的空虛。那個肥婦的樣子我至今還記得。…… “你看,這就是那個以歌德自命的人的遭遇了!”朋友嘲笑地說。 我又想發笑,又不想發笑。我把信箋折好放在信封里還給他。 我們走過一家影戲院。名字很堂皇,可是門面卻很小、很舊。一個木籠似的賣票亭立在外面。 “這樣的電影院你一定沒有去過,不可不進去看看。”朋友并不等我表示意見就去買了票,我看見他從衣袋里掏出了兩個法郎。 “這樣便宜的票價!”我想。我們就進去了。 一個小房間里放了二三十排長木凳,每排三張,每張可容五六個人。黯淡的天花板上掛了幾盞不很明亮的電燈。對面一張銀幕。沒有樂隊,每一個人走過,就使不平坦的地板發出叫聲。房間里充滿了煙霧和笑語,木凳上已經坐了不少的人。 我們在最后面的一排坐下,因為這一排的三張木凳都空著,而且離銀幕較遠,不會傷眼睛。朋友抬起眼睛向四處望,好像在找他認識的人。 他的眼光忽然停留在左邊的一角。他的臉上現出了笑容。他把右手舉起來,在招呼什么人。我隨他的眼光看去,我看見了兩個我見過的人。他們是一男一女。男的是中國人,戴便帽,沒有打領帶,穿一件半新舊的西裝;黃黃的臉色,高的顴骨,唇邊有幾根胡須。他不久以前還在一只英國輪船上作工。右手的大指頭被機器完全切斷了。他的手醫好以后公司給了他五十鎊的恤金,把他辭退了。他到馬賽來,打算住些時候回中國。我在飯店里見過他幾次,所以認識他。女的,我也在飯店里遇見過。她是一個安南人。我不知道她怎樣會流落到馬賽來,關于她的事,我知道的,就是她跟飯店的老板似乎有一種神秘的往來;還有她屬于街頭女人一類的事,我也知道一點,因為在飯店里的笑談中間,找“安南婆”要多少錢的話也常常聽見。我看見她同斷指華工在一起,這并不是第一次。 她跟他親密地談著(她會說廣東話),兩個頭靠在一起。她忽然轉過頭來望著我的朋友笑。我看見她的黑頭發,小眼睛,紅白的粉臉,寬厚的紅唇,充實的胸膛。她輕佻地笑著,的確像一個街頭女人。 電燈突然滅了。 我花一個法郎的代價連接看了三張長片子。眼睛太疲倦了。燈光一亮我同那個朋友最先走了出去,并不管我們認識的那一對男女。 夜接連著夜,依舊是馬賽的夜。 還沒有開船的消息。罷工潮逐漸擴大了。許多貨物堆積在馬賽,許多旅客停留在馬賽。 馬賽憑空添了這許多人和貨物,可是市面上并沒有什么變動。其實變動倒是有的,不過陌生的我不知道罷了。我只看見過一次罷工者的游行。 夜來了,夜接連著夜。依舊是馬賽的夜。 那飯店,那街道,那旅館,那朋友,那些影戲院跟我發生了密切的關系。左拉的小說讀完了,又放回到箱子里去。我不再讀書了。 每晚從飯店出來,我總是跟那個朋友一起去散步。我們不得不經過那條使我最擔心的街道。那些半老的肥婦照例對我們做出媚笑,說著歡迎的話。但是我已經不害怕她們了。 我們每晚總要到一家新的電影院去。所有馬賽的電影院我們差不多都光顧過了。頭等電影院我們自然也去,而且用學生的名義在那里得到了半價的優待。常常我們在勞動者中間看了電影出來,第二天晚上又換了比較漂亮的衣服到頭等電影院去,坐在紳士和夫人們的中間,受女侍的殷勤招待。換衣服的事是那朋友叫我做的。他有過那樣的經驗,他曾經在頭等電影院里買票受到拒絕。 在小的電影院里,我們常常遇見那個斷指的華工和“安南婆”,他們總是親密地談笑著。 我們跟華工漸漸地熟悉了,同時跟“安南婆”也漸漸地熟悉了。我們跟他們遇見的地方有時在電影院,有時在飯店,時間總是在夜里。 另一個晚上我們照例在那個最小的電影院里遇見了“安南婆”。她跟平日一樣地和男子頭靠著頭在談話,或者輕佻地笑。可是男子卻不是平時跟她在一起的斷指華工,而是一個陌生的法國青年。她看見了我們,依舊對我們輕佻地笑,但是很快地又把頭掉回去跟那個青年親密地講話了。 “安南婆有了新主顧了。”朋友笑著對我說。我點點頭。 隔了一個晚上我們又到那個電影院去。在前面左角的座位上我又看見了“安南婆”和她的法國青年。她看見了我們,望著我們輕佻地笑。我們依舊沒有找到斷指華工的影子。 燈光熄了。銀幕上出現了人影。貧困,愛情,戰爭,死。……于是燈光亮了。 一個人走近我們的身邊,正是我們幾天不見面的斷指華工。朋友旁邊有一個空位,華工便坐了下來。他并不看我們,卻把眼光定在前面左角的座位上。在那里坐著“安南婆”和她的法國青年。 “你為什么這兩天又不同她在一起了?你看她找到了新主顧!”朋友拍著華工的肩膀說。 華工掉過了瘦臉來看我們。他的臉色憔悴,可是眼睛里射出來兇惡的光。 “不錯,她找到新主顧了!她嫌我是一個殘廢人,我倒要使點手段給她看,要她知道我不是好惹的!”華工氣憤地對我們說,聲音并不高。 “這又有什么要緊?這也值不得生氣!”朋友帶笑地勸他道。“她們那般人是靠皮肉吃飯的。誰有錢就同誰玩,或者是你或者是他,都是一樣。她又不是你的老婆,你犯不著生氣。” “你不曉得我待她那樣好,她這個沒有良心的。”華工咬牙切齒地說。“幾個月以前法國軍隊在安南鎮壓了暴動,把那些失敗的革命黨逼到一個地方用機關槍全打死。這樣的事三四年前也有過一次。她哥哥就死在那個時候,死在法國軍人的槍彈下。現在她卻陪法國人玩。這個法國人大概不久就會去當兵的,他會被送到安南去,將來也會去殺安南的革命黨,就像別的法國軍人從前殺死她哥哥那樣……”他說不下去了,卻捏緊拳頭舉起來,像要跟誰相打似的。可是這個拳頭并沒有力量,不但瘦,而且只有四根指頭,大拇指沒有了,只剩下一個可笑的光禿的痕跡。他又把拳頭放下去,好像知道自己沒有力量似的。我想他從前一定是一個強健的人,然而機器把力量給他取走了。 我并不完全同意華工的話,但是我禁不住要去看“安南婆”和她的法國青年的背影。他們是那樣地親密,使我不忍想象華工所說的種種事情。我幾乎忘記了在這兩個人中間的生意的關系,我幾乎要把他們看作一對戀人。但是我又記起了一件事。那個青年的確很年輕,他不久就會到服兵役的年齡。他當然有機會被派到殖民地去,他也有機會去殺安南的革命黨。華工方才所說的一切都是可能的。也許她還有一個哥哥,或者兄弟,也許這個法國青年將來就會殺死他,這也是很可能的。這樣想著我就仿佛看見了未來的事情,覺得眼前這兩個人在那里親密地講話也是假的。“華工的話完全對,”我暗暗地對自己說。但是我又一想,難道這時候我們就應該跑去把那兩個人分開,對他們預言未來的事情嗎?或者我們還有另外的避免未來事情的辦法? 我起初覺得苦惱,后來又不禁啞然失笑了。我記起來他們只是兩個生意人,一個是賣主,一個是顧客,關系并不復雜。我這時候才注意地看銀幕,我不知道影片已經演到了什么地方。 電影演完,我們同華工先走出來。他本來想在門口等她,卻被我們勸走了。我們同他進了一個咖啡店,坐了一些時候,聽他講了一些“安南婆”的故事。他的憤怒漸漸平息了,他時時望著他那只沒有大拇指的手嘆氣。 我那朋友的話一定感動了他。朋友說:“你自己不也是拿她來開心嗎?你不是說過一些時候就要回國去嗎?那時候她終于要找別人的。她又不是你的老婆。你有錢,你另外找一個罷,街上到處都是。你看那里不就有一個嗎?”說到這里他忽然舉起手,向外面指。在玻璃窗外,不遠處,一個女人手里拿了一把陽傘,埋著頭在廣場上徘徊,一個男人在后面跟著她。 我們跟華工分手的時候,那個朋友勸他說:“你把安南婆忘了罷,不要再為她苦惱。你只要再忍耐幾天,她又會來找你的。” “我不再要她了!”華工堅決地粗聲說,就掉過頭去了。我仿佛看見他的眼角嵌著淚珠。我不懂這個人的奇怪的心理。 隔了兩個晚上我們又在另一家小影戲院里遇見了“安南婆”。這一次她走到我們跟前來,就坐在朋友的身邊。她不再坐到前面去了,因為她是一個人來的。 “你一個人?”朋友用法國話問她。 她笑著點了點頭,把身子靠近朋友。我不由得想:“她來招攬生意了。” “你的法國朋友呢?”朋友嘲笑地問。 “不知道。”她聳肩地回答。 “從前那個中國朋友呢?” “他是一個呆子。”她直爽地回答,沒有一點顧忌。“他太妒忌了,好像我就是他的老婆一樣。其實我只是做生意的人,誰都管不著我。誰有錢就可以做我的主顧。他太乏味了。我有點討厭他。……” 燈光突然熄了,使我沒有時間問她關于她哥哥被殺的事,或者她究竟還有沒有哥哥或者兄弟的事。我在看銀幕上的人物和故事。金錢,愛情,斗爭,謀殺……。 從影戲院出來,我們陪著她走了一節路,到了一個十字路口,朋友忽然對她說:“你應該往那邊走了。” “是,謝謝你。”她媚笑地對朋友說。“到我那里去玩玩嗎?” “不,謝謝你,我今晚還有事情。改天去看你罷。”朋友溫和地答道,跟她握手告別了。 等那女人走遠了時,朋友突然笑著對我說:“她今晚找錯主顧了。” 這是一個月夜,天空沒有云。在碧海中間,只有一輪圓月和幾顆發亮的星。時候是在初冬,但是并不特別冷。 四周只有寥寥的幾個行人。我們慢慢地走著,我們仰起頭看天空。我們走到了廣場上。 忽然一個黑影在我的眼前一晃,一只軟弱的手抓住了我的膀子。我吃驚地埋下頭看,我旁邊站著一個女人。她的哀求的眼光直射到我的臉上。她的臉涂得那樣白,嘴唇涂得那樣紅,但仍然掩不住臉上的皺紋和老態。是一張端正的瘦臉,這樣的臉我在街頭的賣春婦里面簡直沒有看見過。她喃喃地說:“先生,為了慈善,為了憐憫,為了救活人命……”她的手抓住我的左膀,她差不多要把身子靠在我的身上。她是一個怎樣不熟練的賣春婦啊! 不僅是我呆了,而且連那個頗有本領的朋友也不知道應該怎樣對付了。我茫然地站著,聽她在喃喃地說:“為了慈善,為了憐憫,為了救活人命……” 天呀!這個女人,論年紀可以做我的母親,她卻在這深夜,在廣場上拉我到她家里去。為了慈善,為了憐憫,為了救活人命,我必須跟這個可以做我母親的女人一起到她家里去。這種事情,讀了十幾年的書的我,一點也不懂。我以前只是在書本上過日子。我不懂得生活,不懂得世界。我也不懂得馬賽的夜。 我不知道應該怎樣解決我第一次遇到的這一個難題。然而出乎我意料之外地,她突然跑開了,好像有惡魔在后面追趕她一般。于是很快地她的瘦弱的背影就在街角消失了。 沉重的皮靴聲在我們的后面響起來,接著我聽見了男人的咳嗽聲。我不知不覺地回頭看,原來是一個警察走近了。 我們拔步走了。我起初很慶幸自己過了這個難關,但以后又為這個依舊未解決的新問題而苦惱了。我再一次回頭去看那個婦人,卻找不到她的影子。 “怎么會有這樣多的賣春婦?難道這許多女人除了賣皮肉外就不能生活嗎?”我苦惱地問那個朋友。 “我那個旅館的下女告訴我,半年前她和六個女伴一起到這個城市來,如今那六個女子都做了娼妓。只有她一個人還在苦苦地勞動。她一天忙到晚,打掃那許多房間,洗地板,用硫磺熏臭蟲,還要做別的事情,每個月只得到那樣少的工錢。她來的時候還很漂亮,現在卻變丑了。只有幾個月的工夫!你是見過她的。” 不錯,我曾經在朋友的旅館里見過她。她是一個金頭發的女子,年紀很輕,身材瘦小。現在的確不怎么好看,而且那雙手粗糙得不像女人的手了。 “我想,她有一天也許會(www.lz13.cn)在街頭拉男人的,”朋友繼續說。“這并不是奇怪的事。你不知道在馬賽,在巴黎和在別的大都市,連有些作工的女子也會只為了一個過夜的地方,一個溫暖的床鋪,就去陪陌生男子睡覺嗎?我的朋友里面好些人有過這樣的經驗。也有人因此得了病。……那些街頭女人大部分都有病,花柳病到處蔓延!……我說,在今天的法國社會里,除了那些貴族夫人和小姐以外,別的女子,有一天都會不得不在街頭拉人。……花柳病一天一天地蔓延……這就是今天的西方文明了。”最后的兩句話是用了更嚴肅的聲音說出來的。 他的嘴又閉上了。我們誰都不想再說一句空話。我們依舊在這條清靜的街上慢慢地走著。一些女人的影子又在我的眼前晃,常常有幾句短短的話送進我的耳里。女人們在說:“先生,到這里來”,或者“先生,請聽我說”。可是方才那個使我苦惱的說“為了慈善,為了憐憫,為了救活人命”的聲音卻聽不見了。 這是一個很好的月夜。馬賽的夜。 巴金寫《家》時用的桌凳 巴金作品_巴金散文集 巴金:我的夢 巴金:友誼的海洋分頁:123
馮驥才:死鳥 天津衛的人好戲謔,故而人多有外號。有人的外號當面叫,有人的外號只能背后說,這要看外號是怎么來的。凡有外號,必有一個好笑的故事;但故事和故事不同,有的故事可以隨便當笑話說,有的故事人卻不能亂講;比方賀道台這個各色的雅號——死鳥。 賀道台相貌普通,賽個豬崽。但真人不露相,能耐暗中藏。他的能耐有兩樣,一是伺候頭兒,一是伺候鳥。 伺候上司的事是挺特別的一功。整天跟在上司的屁股后邊,跟慢跟緊全都不成。跟得太慢,遇事上不去,叫上司著急;跟得太緊,弄不好一腳踩在上司的后腳跟上,反而惹惱了上司。而且光是賽條小狗那樣跟在后邊也不成。還得善于察言觀色,摸透上司脾氣,知道嘛時候該說嘛,嘛時候不該說嘛;挨訓時俯首貼耳,挨罵時點頭稱是。上司罵人,不準是你的不是,有時不過是上司發發威和舒舒氣罷了。你要是耐不住性子,皺眉撇嘴,露出煩惱,那就叫上司記住了。從此,官兒不是愈做愈大,而是愈做愈小——就這種不是人干的事,賀道台卻得心應手,做得從容自然。人說,賀道台這些能耐都出自他的天性,說他天生是上司的撒氣簍子,一條順毛驢,三腳踹不出個屁來,對么? 說完他伺候頭兒,再說他伺候鳥兒。 伺候鳥的事也是另外一功。別以為把鳥關在籠子里,放點米,給點蟲,再加點水,就能又蹦又跳。一種鳥有一種鳥的習慣,差一點就閉眼戧毛,耷拉翅膀;一只鳥有一只鳥的性子,不依著它就不唱不叫,動也不動,活的賽死的差不多。人說賀道台上輩子準是鳥兒。他對鳥兒們的事全懂,無論嘛鳥,經他那雙小胖手一擺弄,毛兒鮮亮,活蹦亂跳,嗓子個個賽得過在天福茶園里那個唱落子的一毛旦。 過年立夏轉天,在常關做事的一位林先生,打江蘇常州老家歇假回來,帶給他一只八哥。這八哥個大肚圓,腿粗爪硬,通身烏黑,嘴兒金黃;叫起來,站在大街上也聽得清清楚楚。賀道台心里歡喜說:“公雞的嗓門也沒它大。” 林先生笑道:“就是學人說話還差點。它總不好好學。怎么教也不會,可有時不留神的話,卻給他學去了。不過,到您手里一調理,保準有出息。” 賀道台也笑了。說道:“過三個月,我叫它能說快板書。” 然而,這八哥好比烈馬,一時極難馴服。賀道台用盡法子,它也學不會。賀道台罵它一句:“笨鳥。”第二天它卻叫了一天“笨鳥”。叫它停嘴,它偏不停。前院后院都聽得清清楚楚,午覺也沒法兒睡。賀道台用罩子把籠子嚴嚴實實罩了多半天,它才不叫。到了傍晚,太太怕把它悶死,叫丫鬟把罩子摘去,它一露面,竟對太太說:“太太起痱子了吧?”把太太嚇了一跳。再一想,這不是前幾天老爺對她說的話嗎,不留神竟給它學去了。逗得太太格格笑半天。待賀道台回來,對老爺說了。沒等她去叫八哥再說一遍,八哥自己又說:“太太起痱子了吧!” 賀道台給逗得咧嘴直笑,還說:“這東西,連聲音也學我。” 太太說:“沒想到這壞東西竟這么聰明。” 自此,賀道台分外仔細照料它。日子一長,它倒是學會了幾句什么“給大人請安”、“請您坐上座”、“您走好了”之類的話,只是不好好說。可是,它抽冷子蹦出幾句老爺太太平時說的“起痱子”那類的話,反倒把客人逗得大笑,直笑得前仰后合。 知府大人說:“賀大人,從它身上就知道您有多聰明了。” 賀道台得意這鳥,更得意自己。這話就暫且按下不提。 九月初九那天,東城外的玉皇閣“攢九”,津門百姓照例都去登閣,俗稱九九登高。此時,天高氣爽,登高一望,心頭舒暢,塊壘皆無。這天直隸總督裕祿也來到了玉皇閣,興致非常好,順著那又窄又陡的樓梯,一口氣直爬到頂上的清虛閣。隨同來的文武官員全都跑前跑后,哄他高興。賀道台自然也在其中。他指著三岔河口上的往來帆影,說些提興致的話,直叫裕祿大人心頭賽開了花。從閣上下來,賀道台便說,自己的家就在不遠,希望大人賞臉,到他家去坐坐。裕大人平日決不肯屈尊到屬下家中作客。但今日興致高,竟答應了。賀道台的轎子便在前面開道,其余官員跟隨左右,騎龍駕虎一般去了。 賀道台的八哥籠子就掛在客廳窗前,裕大人一進門,它就叫:“給大人請安。”聲音嘹亮,一直送進裕祿的耳朵里。 裕大人愈發興高采烈,說道:“這東西竟然比人還靈。” 賀道台應聲便說:“還不是因為大人來了。平時怎么叫它說,它也不肯說。” 待端茶上來,八哥忽又叫道:“這茶是明前茶。” 裕大人一怔,扭頭對那籠子里的八哥說:“這是你的錯了。現在什么時候了,哪還有明前茶?” 上司打趣,下司拾笑。笑聲貫滿客廳,并一齊訕笑八哥是個傻瓜。 賀道台說:“大人真是一句切中了要害。其實這話并不是我教的,這東西總是時不時蹦出來一句,不知哪來的話。” 知府笑道:“還不是平日里說者無意,聽者有心。想必賀大人總喝好茶,它把茶名全記住了!” 裕祿笑道:“有什么好茶,也請裕祿我嘗嘗。” 大家又笑起來。但八哥聽到了“裕祿”兩字,忽然翅膀一抖,跟著全身黑毛全日方起來,好賽發怒,聲音又高又亮地叫道:“裕祿那王八蛋!” 滿廳的人全怔往(www.lz13.cn)。其實這一句眾人全聽到了,就在驚呆的一刻,這八哥又說一遍:“裕祿那王八蛋!”說得又清楚又干脆。裕祿忽地手一甩,把桌上的茶碗全抽在地上,怒喝一聲:“太放肆了!” 賀道台慌忙趴在地上,聲音抖得快聽不見:“這不是我教給它的——”話到這里,不覺卡住了。他想到,八哥的這句話,正是他每每在裕祿那里受了窩囊氣后回來說的。怎么偏偏給它記住了?這不是要他的命嗎?他渾身全是涼氣。 等他明白過來,裕祿和眾官員已經離去。只他一個人還趴在客廳地上,他突然跳起來,朝那八哥沖去,一邊吼著:“你毀了我!我撕了你,你這死鳥!” 他兩手抓著籠子一扯,用力太大,籠子扯散,鳥飛出來,一把沒有抓住。這八哥穿窗飛出,落在樹上。居然把賀道台剛剛說的這話學會了,朝他叫道:“死鳥!” 賀道台叫仆人們用桿子打,用磚頭砍,爬上樹抓,八哥在樹頂上來回蹦了一會兒,還不住地叫:“死鳥!死鳥!死鳥!”最后才揮翅飛去,很快就無影無蹤了。 自此,賀道台就得了“死鳥”的外號。而且人們傳這外號的時候,還總附帶著這個故事。 馮驥才作品_趙麗宏散文集 馮驥才名言 馮驥才經典語錄分頁:123
真愛就是一邊嫌棄一邊不離不棄 文/南有 1 我身邊有一對情侶特別受到大家矚目。因為男生是特別帥氣迷人的樣子,而小姑娘卻普通而樸素。 我第一次見到這個男生的時候,直接是被他帥醒的。 他不說話,說話,笑起來,不笑起來的樣子,都是帥的。 身邊很多認識男生的人都很不解,為什么他最后會和這樣一個姑娘在一起。不是沒有長得很漂亮的姑娘追過他,可是他都不動心。 我和這個男生是大學特別要好的哥們。身為一個超級外貌協會者,我最后實在看不下去了,有一回在微信里開玩笑問他,嘿你就不能換一個女朋友嗎? 哥們回我說,張南,你們都覺得她不好看不漂亮。可是啊,在我心里,她就是好看的。 哥們剛開始追這個姑娘的時候,姑娘身邊的朋友都覺得不可思議。畢竟哥們不僅念書成績好,而且籃球打得好,人也長得帥。 這種人丟在花癡泛濫的女生堆里,分分鐘是被搶得渣都不剩的。 而姑娘呢,是一個特別普通的人。長得一般,也沒有什么特別突出的特長。 哥們注意到她,只不過是因為有一次他打完籃球,剛好看到她幫忙剛入校的師妹們拉行李。 明明自己個子小小的,幫起別人來,卻滿身都是力氣。當時他覺得,這姑娘真熱心腸。于是很低調地追起姑娘來。 一開始姑娘都覺得很驚訝,很多人提醒她,說不定他是跟別人打賭了,或者是鬧著玩的。 誰知道后來啊,他們就在一起了。畢業沒有分手,工作異地沒有分手。而且一直到現在,他們就要結婚了。 再后來我問哥們,哥們說,姑娘對他各種好,而且他喜歡她周到細致的心思,可以照顧到身邊所有人的感受。一個懂得為別人著想的人,是善良的人。 或者喜歡一個人,并不是因為她有多好看。你不是傾國傾城,但是卻剛剛好能填滿我的眼睛。 2 都說經常假裝嫌棄你的人,一定是最愛你的人。 第一個嫌棄我長得丑的人,是我媽。 我之前在文章里寫過我媽,她總是能從我身上找到100種我丑的證據。 某一回我們一起在客廳坐著,她看電視,看到一個男明星。 我媽突然脫口而出說,這人怎么這么丑,比我兒子還丑,還是我兒子帥!!! 我當時正玩著手機,聽到這句話正想嘚瑟幾句,心想我的媽啊,你終于認清你兒子的真面目其實就是一個帥哥了啊!有眼光! 結果一看電視,靠,我媽在看電視節目,說的是黃渤…… 媽你別說了,我想靜靜…… 其實吧,爸媽嫌棄自己孩子長得丑,并不是真的嫌棄。 在這個世界上,真正愛我們的,還真是他們。 3 我見過很膩歪的情侶,但是一把年紀還很膩歪的,就屬我大學一女生同學的爸媽了。 兩個人加起來也有100多歲了吧。 阿姨每天都喜歡穿得很時髦,叔叔就負責站在旁邊看。 我同學說,我媽啊,每次出門穿衣服,都要在鏡子面前轉幾圈。 然后回頭問我爸,這衣服好看嗎? 我爸就會一臉色瞇瞇,哦不是,是笑瞇瞇地說:好看,但是你更好看。 我同學跟我描述這一場景的時候,我能感覺到她當時受到的傷害。 我同學說,其實我媽年輕的時候很漂亮的,我爸也很帥。 這么多年來,他們都是這么膩歪的。 看了那么多年,我都看膩了,我爸還老說我媽好看。 這么多年了啊,我媽臉上都是皺紋和斑點了,我爸還說我媽好看。 我聽完她的描述,當時想起了那句歌詞: 多少人曾愛慕你年輕時的容顏/可知誰愿承受歲月無情的變遷/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來了又還/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邊/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邊 這大概就是感情的最美結局吧。 愿我們老的時候,還會有人喜歡看我們臉上的皺紋。 當你嫌棄父母時,請讀這段話 曾經嫌棄過父母的孩子們 IT大佬奮斗史:馬云蹬三輪送書,劉強東創業遭女友嫌棄分頁:123
ACC711CEV55CE
台中中區併購整合會計服務推薦
書店產業節稅方式 台中北屯申請統一發票會計師事務所 健保投保分哪些類別?應分別在哪裡辦理投保手續?



 留言列表
留言列表


